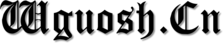Disclaimer: 本人不懂精神分析,这篇文章完全是强行把小说塞到齐泽克的框架里面,依样画葫芦,难免结构松散、错谬百出,请方家指教。 8月12日初稿注:有好多地方是瞎编的,等书看完再改一遍。
我一脚踏空,我就要飞起来了……
这段字面意义缺乏连续性,隐喻和结构令人费解的线索性的歌词,为什么,即使是对其中词语所指乃至故事内容都一无所知的人,也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素描画里面他们空洞却坚定的眼神之下究竟埋藏着怎样的思想?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阅读《撒野》,在情节中找到这种震憾的文本化的具体表现。
再读到《崇高客体》时,我确凿地体会到了既视感,觉得这就是解开歌词中隐喻的钥匙,书中的种种情节都是精神分析中常用比喻的精妙组合。这样的解读让我们理解,为什么看似阴郁沉闷的描写,却蕴藏了最为激进的反抗维度。
按小说的顺序,先从蒋丞说起。
直接将两位作者的文本联系起来的是蒋丞的签名:Last of the Wilds。这首金属交响本名Erämaan Viimeinen,Erämaan 是丰富,丰饶的野地、狩猎场,Viimeinen 是最后、最终、临死前的。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签名直截了当地与“实在界之荒漠”的比喻向重合,阐释出蒋丞作为救赎者和圣徒的基本行为模式:他所承受的正是作为大他者欲望的实在界原始丰饶之剩余,他生来就是实在界荒野的剩余。 作为歇斯底里的厂区原生家庭的遗孤,面对城市家庭教育的询唤和异化,他首先以焦虑化的态度固守抵抗的内核,并由于这种秩序与异性恋规范的混淆而形成了象征型的同性恋模式。至少在早期,他一直把这种剩余作为自身身份之代表来认同,而来到钢厂以后,“遗孤”更是一步步成为他不可摆脱的身份。这种对死亡驱力的认同也可看作是基督教圣徒的行为模式之一端。 另一方面,按上文的对应法,回到厂区的经历无异于与实在界本身的一次亲密接触,直接触及了无以言表的创伤内核,这也是蒋丞所踏之“空”。 厂区的家庭生活是征候性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实问题。家人和街头青年的行为模式,从蒋丞这样的局外人视角来看,其无意义的同义反复的自我循环特性昭然若揭,它的小客体剩余直接暴露在蒋丞的眼光下,成为创伤可感的实在界暴露之体验。这一时刻的“起飞”,不是自由的飞翔,而是身处实在界的裂隙、自由之深渊上方,是被恐惧充满的惊魂一刻。
我向上是迷茫,我向下听见你说这世界是空荡荡 你说一二三,打碎了过往,消亡
蒋丞在这里经历的痛苦无疑是真实的虚无的后现代性体验。向上,是幻象消灭后的无意义之迷惘,向下,是彻骨的实在的空虚。这里的“你”与其说是蒋、顾二人中的对方,毋宁说就是母亲-大他者,是对原始享乐的统一体的怀恋;无怪乎蒋丞还在对沈一清的称呼上嘴瓢,顾飞还在犹豫要不要剃掉鬓边的休止符(也就是不存在、不可能的原质,这同时也是他幼时与丁竹心的统一体的残余)。蒋丞在蒋父的病(父之名)的质询下,受到沈一清反复的“意欲何为”之问,终于“打碎了过往”的幻象,陷入了原始的疯狂,最终在顾飞家门口一脸栽倒在地。而顾飞,那个从小在厂区长大的、无论从表情上还是行动上看来都对一切痛苦不以为意的小店主人,也早已从类似的途径来到同一片荒原之上,或者说,他从来未曾离开。
起初我也觉得,遗弃-收养-弃养-丧父这样的情节设置过于极端了,但后面的发展让我看到,正是作者把主人公的境遇写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这种气魄,为后面新的救赎之路的展开铺平了地基。(当然这相比社会现实中还是有所夸张了,不过也正是这个夸张,再次印证了现实生活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道理;具体家庭的现实情况读者自然会具体考虑。)
有风吹,破了的归途,你有没有看到我在唱
回归母体的归途一断,主体被从意义的世界中抛弃出去,流落于无意义的荒原之上,他唱出的歌就不再具有意义,除非他被另一个主体纳入视野,借助主体间的移情重建意义之维。
你说一二三转身,你听被抹掉的慌张
丞飞相认经历了经典的双向误认过程。顾飞对蒋丞的移情过程完成于看到蒋丞的弹弓表演与哭泣,而蒋丞那边则要等到顾飞腾空飞起的那个时刻。如果要仿照《傲慢与偏见》的格式为这段故事命名,题目无疑也可以是《高贵与顽强》之类的,也就是BL评论者常说的“学霸与学渣”,后者没有看到的是这两个词语恰恰并非两人真实性格的体现,而是初识之际对对方品性的误认。之所以从顾飞所在的楼顶看来“丞哥无处不在”具有戏剧性的振憾力,也是因为在这里蒋丞作为顾飞的移情之幻象的功能被发挥到了极致。作者在这里显然是刻意地插入了带有魔幻现实色彩的描写,用以放大这种效果。蒋,苽也,丞,承也;蒋丞生于荒野,归于承受。相比之下,顾,虑也,顾飞生于忧患,当他把忧患投入爱情,化为力量,便能飞跃至彼岸。他固守摆脱帮派斗殴而投入爱情的欲望,借助“丞哥无处不在”这个幻象建构,跨跃了是实在界的不可能的鸿沟,抹除了起跳时的“慌张”,这里的“你”也终于成为情侣之间的称谓。
另一方面,两人在升学之后遇到的困境则已经处于真实的社会结构这样的大他者语境之中了;在这里我们不出所料地再次看到蒋丞以他隐忍的态度完成了爱情信仰对社会结构压力的抵抗。 相对地,顾飞直到提分手那次以前长期处于的是一种犹太教式的焦虑状态,这种状态是出于对于实在的钢厂社会状况的深切感知产生的自发的抵抗。他从来不愿、也没有通过幻象来屈从生活境况为他规定的条条框框,而是在自己的帮派生活中完成意义的建构,而在社会生活领域保持焦虑。 顾飞的家庭背景为想象界同性恋倾向的形成提供了温床。蒋丞作为厂区出生的婴儿的时期无疑也有这种条件,但童年压抑的城市生活无疑给他的行为模式埋下了更多对符号秩序的反抗的色彩。于是,蒋丞欣赏顾飞,更加直接而主动,一旦在醉酒中失去理性的自制就身不由己地陷入其中,这种激情不仅与身体的吸引相联系,也与生活中的忿懑情绪一脉相承;相比之下,顾飞的感情更加沉郁和内敛,几乎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理性决定(这里又类似于《理智与情感》的对立),他的爱更要从身体开始,并且不得不同他与他家庭中女性亲属的关系相协调。
在丞飞爱情炽烈燃烧的同时,另一方面,作为顾飞的无意识的代言的顾淼仍然处于失语状态,无法被解读。这意味着顾飞在社会生活上的焦虑仍然在阻塞他在社会领域的符号认同。于是,故事的结局与其说是作为荒野遗孤的两个人最终在新的城市中找到了新的希望,不如说是蒋丞的坚忍让顾飞同样找到了基督教意义上救赎的路径,他们终于可以一起直面未知的困难(顾淼未来的治疗,两人未来的工作压力),在反抗社会压力的过程中用对“承受”的信仰取代难承其重(更好的说法是轻)的爱情成为新的支柱,用无处不在的“承受”彰显了更加激进的反抗维度:他们终于做到了“都像对方一样勇敢”。从这一点上说,批评许行之的心理治疗的非本质的行为学方式或学科传统,或说新自由主义的布尔乔亚态度,是无效的,因为许的帮助的关键不在于直接用他的心理学疗愈顾淼本身展现出的征候性失语,而在于使全家走上了救赎式的行动之路,通过对死亡驱力的行动式认同真正同这种征候体现的剩余开始抗争了;也正因为如此,丞、飞承认了顾淼说话的困难而不再自欺欺人地将错就错,不再将就她简化的语言,顾淼的征候也得到了逐步的化解。
我想,抬头暖阳春草,你给我简单拥抱
在最终这组场景的背景的“暖阳春草”中,荒草原如悖论般再次出现,不同的是,爱情的暖阳照耀在了荒芜的草原之上。这是对实在界的最终回归:通过相伴终生的日常生活,置身虚无的托乐思式迷惘终于结束,钢厂的回忆、生活的荒芜的真相共同构成了丞飞爱情信仰的坚实内核。在这一点上,《撒野》无愧是远迈《红楼》的富于启蒙精神的杰作,从而为“无立足境”之后的主体重新建立了对生活的信仰和热情。如果说《红楼梦》在哪一点上超越了三百年后的这本小说,那也是在于它对社会生活领域更加细致而广阔的描绘和真实的还原对读者生活的启迪,在这一点上,《红楼梦》超越了它的题旨,以作者自身更为艰苦卓绝的写作-生活,在实践的层面上为读者提供了更强大的精神力量。所以,无论更爱哪一本,都要投入社会的实践之中,用自己圣徒般的信仰去直面死亡驱力,去克己地生活。
我想,踩碎了迷茫走过时光,睁开眼你就会听到
——穿越幻想,进入生活,爱情不死,互为对象。对方的凝视与自身意义的构建的关系在视与听的通感的再次出现中以更肯定的语调再现。
我想,左肩有你,右肩微笑
——恰恰是作为承担者,主体获得了快感(强强文的精髓就是双向的保护欲==)
我想,在你眼里,撒野奔跑
——在对方的凝视之中,主体建构起新的幻象,使幻象欲望得到了完满的释放。
(间奏)
作者有意标明的间奏也在后来的谱曲中得到了近乎夸张的呈现,为欲望自由的循环流动留足了空闲,直到最后停留在这段爱情的根本幻象的两个要素的重合$◇a之上:
我想,一个眼神,就到老
——瞬间(眼神相对,小客体欲望重合,误认形成)成为永恒(主体一生的实践)。
本站文章除注明转载/出处外由 wguosh 创作,均为本站原创或翻译,采用 知识共享署名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转载前请务必署名
最后编辑时间为:2021-08-12 18: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