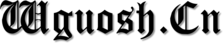自译 根据 The Adventure, Giorgio Agambe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Lorenzo Chiesa, MIT Press, 2018. L’avventura, Giorgio Agamben, Nottetempo, 2015. 第四章
4 事件
事件不是发生之事 —吉尔$\cdot$德勒兹
###
在1952年,卡洛$\cdot$迪亚诺「主要研究伊壁鸠鲁等人的哲学、宗教学家」在《意大利哲学批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形式与事件》可能是他最富雄心的理论著作。 文中他把形式与事件对立了起来。形式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 eidos「理型,犹言idea,是超验的、由精神看到的形态」,它不参与到任何关系以内,就已经自在地完成了,不会更变;事件则总是铭刻进了一段关系中,无法实体化为一种本质(而斯多噶主义者则以本质为其思想的一个中心概念)。 我们关心的不是这组对立,也不是讲清楚迪亚诺用来解读希腊世界的这两个范畴,而毋宁是他对事件的定义,追溯到了 tyche 堤喀。 他注意到,tyche派生自tychano(发生),是用不定过去时「不暗示持续或完成的过去时态」构造出来的,因而指的是一种暂时和未选定的发生,在此意义上也就是moira和heimarmene的对立面——后者则是用完成时构造出来的,暗示了已然之事的必须和不可变异。 在此意义上,tyche无异于“对事件的假设化”(Diano,20)——不是对于冷漠随机的事件,而只是说它发生于某人。 “所以,事件就不是随便什么事件,而是对于每一个人的事件。…… 这是关键的区分。 下雨了,这个事实是发生「accade, ad- (“to”) + cadere (“fall”)」之事,但这不足以使它变成一个事件;它要成为一个事件,必须由我把这种发生的事感知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ibid., 72)。
很容易从这里认出骑士奇遇的特征:奇遇总是直接关涉于其中生活的骑士。
如果说作为事件e-ventus「eventus = ex-(“out of”) + veniō (“come”) + -tus」,它忽然就发生「avviene = ad- (“toward, to”) + veniō」了,我们也不知其所从来,那么作为奇遇ad-ventus「ad- + veniō + -tus」,它总是只在给定地点发生在某人身上,而且只为他而发生。
正如迪亚诺所写,“事件总是此时此地「hic et nunc」”(ibid., 74)。
There is an event only in the precise place where I am and at the moment when I perceive it” (ibid., 74).
通过发生(avvenendo),奇遇要求“有某个人”来让它发生在他身上「a cui avvenire」。
不过,这不是说事件——这个奇遇——依赖于主体:“并不是此时此地「hic et nunc」选定了事件的所在并限定了事件的时间「把事件局域化、暂时化了」;是事件限定了此时「nunc」的时间「暂时化了此时」,并选定了此地「hic」的所在「局域化了此地」”(ibid.)。
这位“某人”不是作为一个主体事先存在了的——我们毋宁说,这场奇遇主体化了它自身,因为“于某地在某人身上发生”(l’avvenire)是它的一个构成性部分。
###
埃米尔$\cdot$本维尼斯特表明过,“这里”和“这时”与指称词典性现实的术语不同,它们是像代词“我”和“你”那样,是暗示着阐述的。 就是,这些词有一层意思是只关系于用到它们的话语之实例的,归根结底只是关系于讲出词语的说话人。 正如“我”这个主体可以只用短语locution定义,从而是说出当前话语之实例中的“我”这个词的这个人,所以“这里”和“这时”不可以客观地识别;毋宁说,它们分隔「delimit」与包含“我”的话语之实例共存而且同时的空间和时间的实例。
然后知何以此事件总是语言之事件以及何以此奇遇与讲述它的言语不可分隔。 此时此地发生的实存是发生于“我”身上的,是故与语言不无关系;它毋乃是每次都相对于一个阐述之实例而被再次定义了;它总是“可说者”,如此而要求被说出。 是故,牵涉于此事件-奇遇中者,是作为说话的实存牵涉和召唤于中的,依照必要的圆桌法则,他也必须试图讲述其奇遇。 此奇遇呼唤他进入到言语之内,而又是正在由它所呼唤之人讲述的,在此言说之前并不存在。
###
早在1908年,埃米尔$\cdot$布莱叶在其令人望而生畏的巨著《古代斯多噶主义中的虚体之理论》中就关注过事件的虚体特性,以及它们与卓越绝伦之虚体「incorporeal par excellence」的联结,这种虚体被斯多噶主义者指称为lecton,“可说者”(或者按布莱叶的偏好称为“可表达者”)。 可说者这种东西,不仅仅是语言,又不仅仅是事实;古人有云,它处于思想和原质、言语和世界的中间。 它不是与言语分隔开来了的原质,而是只在被说出、被命名的层面上的原质;它也不是作为自治符号的言语,而是正处于命名和宣示原质的行动中的言语。 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在于其纯粹可说性的原质、是原质在语言中的发生「happening」。 在1969年,为了复现布莱叶在《感觉的逻辑》中的理念,德勒兹写道,“此事件不是发生之事「what happens」(偶尔的事故accident),毋宁,它是在发生之事之中的,纯粹的可表达者,发出信号并等待着我们”(德勒兹,170)。 在此意义上,它是这样的东西:经历「occur to」此事件的人在顺从和怨忿之外,还必须欲望它、爱它,因为他为了不辜负对它的信仰,首先最早在发生之事「what occurs」中看到牵涉到他而他必须承认的这场奇遇。
必须指明,个体要接受发生「avviene」在他身上的奇遇,关键不在于主体的自由选择;这不是自由的问题。 欲望着此事件,只是意味着把它感觉成是自己的,冒险「venturing」进入其中,即,完全面对它的挑战,但不需要有类似决定的东西。 只有如此,事件才已不依赖于我们,才变成了一场奇遇;它成了我们的,或者毋宁说,我们成了它的主体/臣属。
应该从这一视角温习尼采式的教条“爱之命运”「amor fati」。 命运和奇遇,阿南科和堤喀,并不重合。 接受这“最可怕的思想”,欲望着事件被无限重复,这是奇遇的反面。 如同骑士文学对所有人清楚表明的,这样不是因为奇遇不能是重复的,而是因为它在客体这边没有必要性(事件自身是纯粹偶然的),在主体这边也没有对意志的最高肯定——它渴望着永恒的回归,更主要的是渴望自己。 冒险进入此事件的人无疑是爱着、颤抖着、感动了的——但是,即使他最终能够找到他自己,他也不得不在其中轻而易举地完全丧失自身。
###
即使是斯多噶派的教条,据之人必须欲望并欣然接受此事件者,也部分地违背了我们试着要定义的奇遇的含义。 如马库斯$\cdot$阿累尼乌斯所写,
你必须满足于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原因有二:一则因为,这些事是为了你才有了如此历程,它是为你预订的,它专门与你相关,从最古老的成因开始就与你的运命交织在一起;二则因为,发生「accade」在个别每个人身上的事情都有利于达致繁荣与完美,而且,对宙斯来说,也有利于保全宇宙的统治者。 如果你把自己从联络、成因链及其组成部分之中移除,那就像是把宇宙肢解了一样。 只要它取决于你,你就在你为这些事件感到不快时打破这个联络,并在此意义上毁灭它们(V,8,13)。
在这里,欲望着此事件,意味着不与反对或者遮蔽它,而只是这样,随它发生,以有利于造成它。 但是最终,这只是一种泰然自若「impassibility」的形式,也就是说,要知道,自在的完美事件,终究是中立的,重要的只是个体通过接受这些事件从中取得的用处。 这样,事件与主体分隔开了,而事件与它所发生于上之人的统一性、构成了此奇遇的统一性,被破坏了。 因为只有在他把自己整个的带着烦扰投入进去的那场奇遇之中,珀锡瓦尔才知道他自己和他的名字;只有通过冒险、不顾他导航员的警告进入迷人的城堡并躺在奇迹之床上,高文「Gauvain」才完成了他的故事和他的运命。
###
从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开始,海德格尔的思考越来越多地关注了一个词,即Ereignis,他思想的所有不同支线似乎都汇聚到这个词上。 这个词,海德格尔试图追溯到动词eignen,“适合”,以及形容词eigen,“本己的”,在德语中只是指“事件”。 然而——就黑格尔的“绝对”「Abssolute」而言——事件中的问题毫不少于存在的历史「history of Being」的终结,即形而上学的终结。 在《时间与存在》(Zur Sache des Denkens, On Time and Being)中,海德格尔指出,如果形而上学是对存在「Being」的一次次划时代的发送「epochal sendings」的历史,每次发送之后,存在「Being」仍然隐匿其中,以至于出现了的只是一些存在物「beings」,那么对于“居住在事件之中一个思想「thinking」来说……存在「Being」的历史就到达了终点”(海德格尔,《时间》,41)。 换句话说,在事件中出现过去了或发生了的是超越存在与存在物「Being and being」之间的本体论/存在论差异的一种存在「Being」,而且它先于其时代性的目的地「epochal destinations」。 这里的问题是去思考Es gibt Sein中的Es,Es gibt Sein意即“有存在/它给出存在”「There is/it gives Being」。
然而,关键在于,在事件中,受到质疑的不是只是存在「Being」,而是存在与人「Being and man」的共同归属和相互占有「cobelonging and reciprocal appropriation」。 正如海德格尔在《同一与差异》中所说,身处事件之中实际上意味着“体验那种存在与人在其中相互占有「appropriation」的占有「Eignen」”。事件之为事件首先就是关于人性与存在「humanity and Being」的共同存在着「being」的状态(“事件把人和存在「man and Being」安排到「appropriates to」它们的本质上的同在「Zusammen,togetherness」上去”——海德格尔,《同一》,38)。
既然人不比存在「Being」而存在「preexsist」,存在「Being」也不先于人而存在「preexist」,这就意味着,事件中讨论的问题,可以说是事件之事件,也就是人「man」之成为人类「human」。 在存在「Being」发生到他身上的时刻,就存在「Being」发生到了他身上而言,生命体成为了人——它成为了此在「Dasein」;这一事件同时也是人类起源/生成「anthropogenetic」的和本体生成「ontogenetic」的;它与人之成为说话者以及存在「Being」对言语和言语对存在「Being」的发生相重合。 海德格尔因此可以写道,语言是与事件共存「coessential」的。“只是在我们的本质适合于「is appropriate to」语言这一层面上,我们才居住在事件中”(同上)。
正因此,我们一直试图定义的冒险有可能呈现出与Ereignis的若干类似性。 不仅事件和言语是一起在奇遇中给出来的,而且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奇遇也总是要求有一个主体,它发生在这个主体身上(avviene),而且必须得到这个主体的讲述。 此外,主体并不真正先于这场奇遇而存在「preexist」,仿佛奇遇的发生「put into being」取决于他。 相反,他派生自它,几乎好像是奇遇主体化了它自身,因为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发生在某人身上(avvenire)是它的一个构成性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始他的冒险之前,珀锡瓦尔没有名字,而只有在冒险结束时,他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威尔士人珀锡瓦尔。 就像Ereignis中的存在和人「Being and man」那里一样,在冒险中,事件和骑士是一起给出的,作为同一个现实的两副面孔。
###
奇遇的用处是让生命体「the living」成为人类「human」,这个事实也包含在玛丽$\cdot$德$\cdot$法兰西的一首绝美的莱歌中《狼人》中。 这首莱歌讲,有一位男爵,每周有三天,他都会把衣服藏在石头下面,然后变成狼人(Bisclavret),住在树林里劫掠(Al plus espès de la gaudine / s’i vif de preie e de ravin-ll. 65-66)。 他有个爱着他的妻子,她对他的缺席产生了怀疑;她设法让他坦白了他的秘密生活,并说服他向她透露他藏衣服的地方——尽管他知道,如果他丢了衣服或在穿衣服的时候被发现,他将永远只能作狼。 女人找了一个同伙,后来成了她的情人,从藏身处把衣服偷走了。男爵只得一直作狼人,直到有一天,遇到了国王,这才找回衣服,变回人形。
这首莱歌明确地把从人到狼、从狼到人的变换称作“奇遇”。 丈夫的坦白被称为s’aventure li cunta(l. 61),正是这种“奇遇(冒险 )”吓到了女人,促使她背叛了丈夫(de l’aventure s’esfrea-l. 99)。 男人脱下衣服后又穿上的那一刻必须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发生,这种特殊的保密性正显示出,这首莱歌的关键正是动物变成人和人再变回动物的门槛。 跨国这个门槛就是奇遇中的奇遇(冒险中的冒险)。
###
在这个意义上,“奇遇/冒险”是对Ereignis最正确的翻译。 因此,后者是一个真正的本体论术语,就它会发生(到人和语言身上)而言,它命名了实存「Being」,就它会说出和揭示实存「Being」而言,它命名了语言。 因此,在骑士诗中,不可能将作为一个事件的奇遇与作为一个传说故事的奇遇区分开来;因此,通过遭遇这场奇遇,骑士首先遭遇的是他自己和他最深处座位上的实存「being」。 如果奇遇中的事件不外乎是人类的起源/生成「anthropogenesis」,也就是说,由于一种我们无法知道其模式的变换,只是为了重新表述它们,生命体将他的生命与他的语言分开了,这意味着,通过成为人类,他将自己投入到一场仍在进行中的冒险,其结果很难预测。
###
卡尔$\cdot$罗森克朗茨曾经敏锐地观察到,圣杯「the Grail」——他定义为“一种符号”——“成为了有意识实存「being」的行动的原因,因为它本身没有历史,而只是在他们与它的关系中获得了历史”(罗森克朗茨,57)。 在克雷蒂安的《珀锡瓦尔》中,圣杯没有任何神圣之处;它只是一个贵妇人拿在手里的贵重金属容器,而英雄并没有特别注意它。 它类似于那些神秘的客体——如约翰$\cdot$休斯顿电影中的马耳他之鹰——为了这些客体,主人公可以准备去杀人或危及自己的生命,但最终却发现它们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 神学家和诗人后来才将圣杯「the Grail」赋予宗教意义,并将其与最后的晚餐中使用的圣杯「chalice」相提并论,后者也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夫收集十字架上基督伤口流出的血液用的是同一盏。
在这个意义上,圣杯「the Grail」是代表奇遇的完美密码。 人类起源/生成的事件没有自己的历史,因此不可理解;但它却将人类都抛入了一场仍在继续发生(avvenire)的奇遇。
本站文章除注明转载/出处外由 wguosh 创作,均为本站原创或翻译,采用 知识共享署名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转载前请务必署名
最后编辑时间为:2021-10-12 00: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