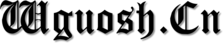自译 根据 The Adventure, Giorgio Agambe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Lorenzo Chiesa, MIT Press, 2018. L’avventura, Giorgio Agamben, Nottetempo, 2015. 第五章
5 厄尔庇斯
有希望,但不属于我们。——弗兰茨$\cdot$卡夫卡
每个人类都身陷奇遇之中,因此,每个人类都得和代蒙、厄洛斯、阿南刻和厄尔庇斯打交道。 它们是奇遇——也就是堤喀——每次展示给我们的不同的面孔或者面具。 当奇遇展现为代蒙之时,生活显得很美妙,简直好像每种情况、每次新的相遇都有一种外力支持着、引领着我们似的。 然而,美妙很快让位于幻灭;代蒙般的东西把它自己扮成了一种例行公事;那种带领生活的力量——亚列Ariel,格尼乌斯Genie,或者缪斯Muse——黯然隐匿,仿佛一个不守诺言的骗子。
事实上,人要对自己的代蒙保持忠诚,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投身于它他、自信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引领我们走向成功,如果我们是诗人,就让我们写出最美的诗,如果我们是感性的人「human beings」,就赋予我们幸福和快感。 诗和幸福不是他的礼物;毋宁,代蒙他自己才是幸福和诗在它们令我们更始「regenerate」、重生「new birth」之时奖励我们的终极礼物。 代蒙犹如伊朗神话中的妲厄娜Daênâ,虽然我们死后才来找到我们,但却是由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善行恶行塑造给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写作以及生活形式用这个新的生灵取代了我们相信自己所是的那个有命名的个体——代蒙是匿名的作者,是守护神「genie」,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写作以及生活之形式归于他,而不必对他怀有任何羡慕和嫉妒。 他被称呼为“守护神”「genie」,不是因为像古人相信的那样、他生成了「generated」我们,而是因为,他给了我们新生,从而打破了把我们与我们旧有的出生相联络的纽带。 这意味着,离别的时刻是代蒙的构成性的所属,我们遇见他的那一刻,就必须从我们自己中分离出来。
据说,代蒙不是神,而是半神。 而“半神”只能意味着神性的潜能和可能性,而不是神性的确实性。 与潜能维持关系是最困难的事情,就此而言,代蒙是我们不停丧失着的东西,对于它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忠诚。 诗性的生活是这样的,在每场奇遇之中,它都让自身与此保持关系:是与一种潜能,而不是一种行动,一个半神,而不是神。
不仅给予我们以生命、还能给予代蒙以生命的令人更始的潜能之名是厄洛斯。 爱当然意味着“被承担和携带”「to be carried」、把自己无保留无顾虑地放弃给奇遇和事件;然而,在我们放弃自己去爱的这个行动本身之中,,我们知道,我们之中的某些东西滞后了、缺失了「in defetto」。 在奇遇中,厄洛斯是构成性地超出了奇遇的潜能,正如奇遇超出、超越了他发生(avviene)在其身上的那个人。 爱比奇遇更强——可能正是这一点促使但丁退出了骑士诗歌的魔法般循环。 但也正因此,在爱情中,我们每每体验到我们的无力去爱,无力去超过奇遇和事件。 正是这种无能为力是引领我们我们去爱的驱力。 似乎,我们对爱的无能为力在爱中展示得越清晰,爱就越是在燃烧、浸满了怀念。
这些感官的完满是“死亡的小秘仪”(古人对睡眠的称呼),通过它,我们试图克服我们对爱的无能。 其中,爱似乎几乎被消除了,和我们告别了——不是因为幻灭和悲伤,像是那种布尔乔亚式的想当然的偏见中那样,而是因为在这种满足中,情人之间失去了他们的秘密,也就是说,互相坦白了他们没有秘密的事实。 但是,正是在这个双向的对秘仪的祛魅之中,他们(甚或他们体内的代蒙)取得了一种新的更受祝福的生活,非动物、非神性,也非人类的生活。
在此意义上,爱总是无希望的,而希望却只属于爱。 这是潘多拉神话的终极含义。 作为最终的礼物的希望停留在了盒子里,这一事实意味着它并不期待它在世界中的事实性达成——也不是因为它把它的完满推迟到了不可见的远期,而是因为在某种方式上它总是已经被满足了。 爱因想象而希望,也因希望而想象。 它希望什么? 它希望满足吗? 非也,因为希望和想象本质上是连系于某种无法满足之物的。 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欲望获取它们的客体,而是因为,它们的欲望,就它被想象和希望着而言,总是已然满足了的。 因此,圣保罗的声言“在希望中我们得救”(《罗马书》8:24)既对又错。 如果希望的客体是无法满足的客体,那么只有作为无法得救者——也就是已经得救者——我们才曾经希望着得救。 正如希望克服了它的满足,它也一样超过了拯救(以及爱)。
本站文章除注明转载/出处外由 wguosh 创作,均为本站原创或翻译,采用 知识共享署名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转载前请务必署名
最后编辑时间为:2021-10-12 17:48:00